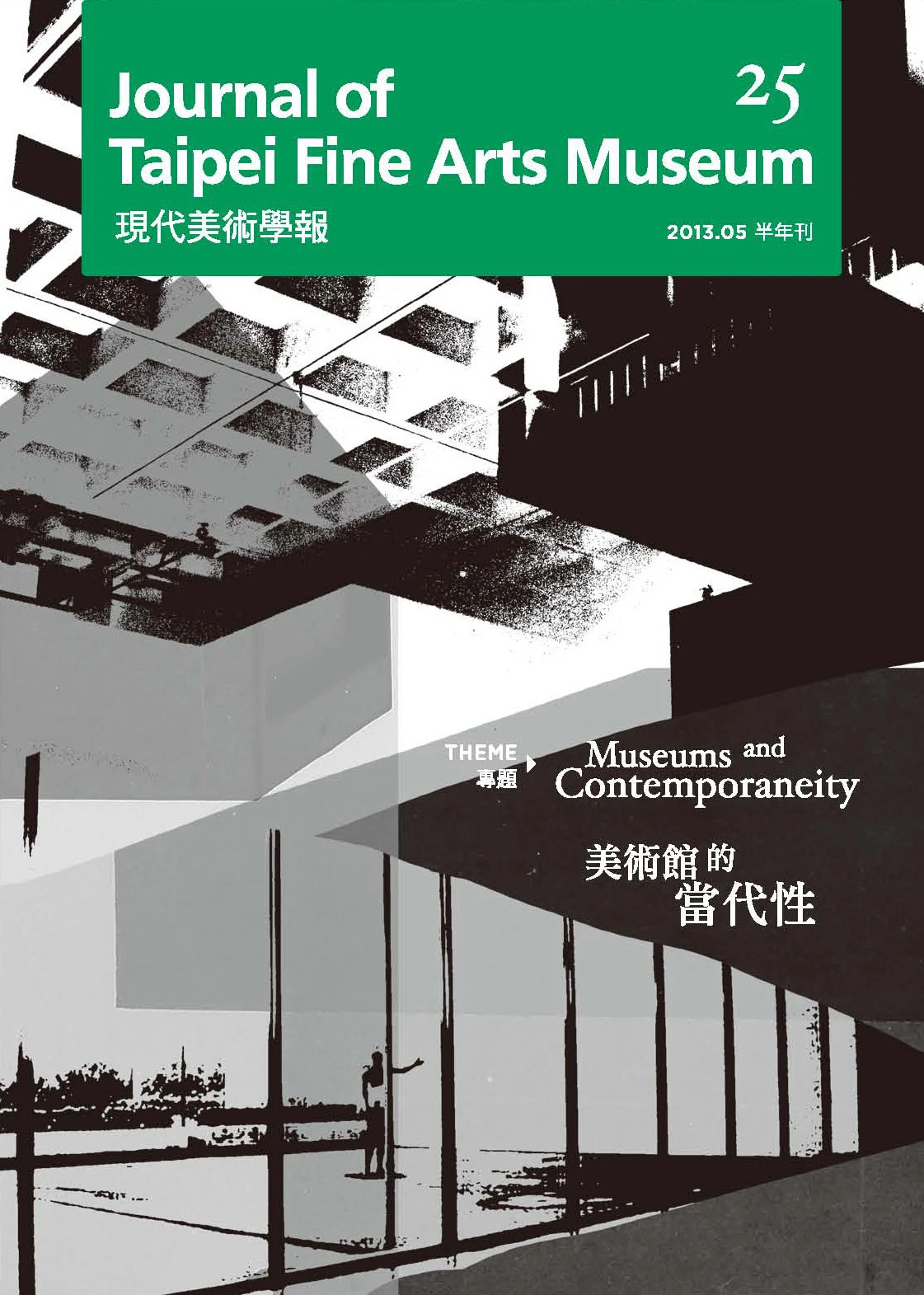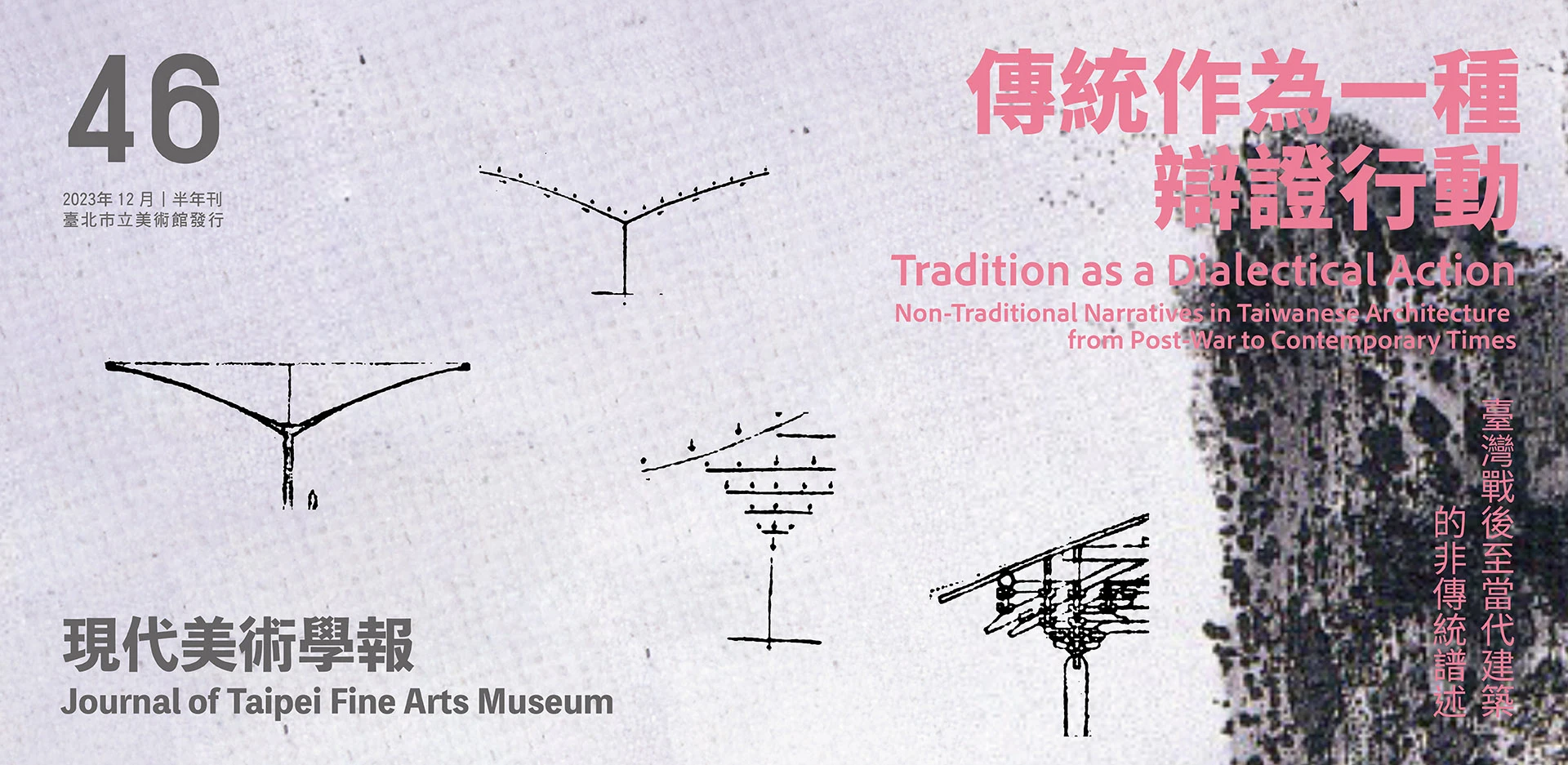摘要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
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英國的文學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以法國大革命為時代背景撰著的小說「雙城記」,發人深省的這一段開場引言,廣泛地被後世引用為正面積極的價值觀和負向的評價意義之對照。
登上藝術創作的舞台,藝術家所扮演的「化身」和「自我」,就像狄更斯「雙城記」裡頭所描述的「人性本質」和「世俗行為」表裡交互糾葛的情節。「化身」和「自我」兩座城堡,時而對峙、時而互補,有時候還來上一段超出邊界的脫稿發揮。然而,更重要的卻是在故事背後所衍伸的意義。對應「自我實現」的人生價值,「利益的誘惑」實質上在藝術創作的領域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自我」的認知必需建立在他人的價值判斷與肯定上,「自性」的發揮將無從而起,而「人性」的許多弱點反而會趁虛而入。
古今中外無論藝術家在創作形式上是奔放或是拘謹,當他們面對深層自我的表述,「眞誠與否?」觀眾很容易就能從創作者「如何看待自我」、「如何闡述自我」的「自畫像」上所呈現的概念分辨出頭緒,尤其檢視一位藝術家是否完全投入創作,是否毫無顧忌的釋放自我?自古以來,畫像反映了畫者觀察自然的深度,也反射了他/她內在的「自我觀照」。從文學和藝術的創作角度甚至深觸宗教問題到人生問題,文藝作品在力求完美之餘,還包含了揭露藝術家自我期許的潛在能量。肖像畫「像不像」的問題固然困擾著東方藝術家,同樣的,自畫像「要不要像」、「像什麼」也困擾著西方藝術家。
本年度出版的《現代美術學報》第 18 期,雖然經過了一番改頭換面,在學術領域爲讀者和學者們尋找良師益友切磋藝事的期許依然堅持。這一期學報中我們選刊了劉俊蘭女士的〈時代容顏:貝何納賀.洪西亞克(Bernard Rancillac)1966-1980 年間的肖像畫〉、黃素雲女士的〈恩索爾藝術中的恩索爾〉、簡瑛瑛女士和彭佳慧女士師生合作的〈性別.階級.族裔:跨國女性藝術的身分認同與自我再現〉以及黃士誠先生的〈兩個芙烈達.卡蘿:森村泰昌之邊緣凝視〉等四篇論文。
這四篇論文,無論是個別藝術家的論述,或是主題論述涉及到了歷史與時代的集體傾向,多少都涉及了「肖像」的意涵和「自畫像」自我認同的省視。儘管寫作主題的動機和研究方法各異,這四篇文章卻在共同的議題上發表了作者對於「認同」與「自省」案例的觀察論述,現代版肖像和「自述」介於藝術創作與觀賞的糾葛情節,似乎也有「雙城記」異曲同工的隱喻,非常有趣。
化身成像
貝何納賀.洪西亞克從抽象創作的自由國度轉進,他所運用的美術素材和法政論點在兩極化的表情國度大大的發揮,洪西亞克的肖像創作衍伸出「自像」的心象觀察,劉俊蘭〈時代容顏:貝何納賀.洪西亞克 1966-1980 年間的肖像畫〉提出了法國藝術家貝何納賀.洪西亞克(Bernard Rancillac, 1931-)在六○年代創作高峰期的肖像畫新解,完全顛覆了「肖像」被視為單純敘事的代言功效。她舉貝何納賀.洪西亞克在 1966-1980 年代的豐富「敘述性」具像意義,以及戰後獨有的「解放」時代潮流,洪西亞克的作品一路追隨政治氛圍,劉俊蘭論證洪西亞克運用「肖像」的符碼意涵操作「政治認同」與「時代精神」,實踐他創作所針對的叛逆世代的「叛逆」,並藉由肖像「與歷史交會」。
花幾分鐘找到「我」
普普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 1928~1987)曾說:「未來,每個人都有成名十五分鐘的可能」,我們推衍他所秉持的理由是生活在這個世上的每一個人,至少都有機會創作一件屬於自己的藝術品;以「藝術家」的姿態呈現自己在個人的「歷史紀錄」當中。的確,二十世紀世界文明史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紀錄」,觀察上世紀末至本世紀的現今,安迪.沃荷的名言確實產生了絕大的影響力,數位影像的重複印製即是明證。在臺灣的大街小巷常見妙齡少女人手一個數位相機,出門在外不消十五分鐘,極可能就完成一組自拍照片公佈在網路上,被識與不識者「點閱」。換句話說,這些歷史紀錄的存在已經不僅只有十五分鐘而已,自畫像和自拍心理無非也滿足了「成名」和「窺視」的現代生活型態。
藝術創作追求的「完美」非僅呈現於藝術品的「品相」,藝術家以作品呈現「自我」,還包含了創作表現時的心靈狀態。有些藝術家專以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來體驗、嘗試人生,卻用易容變裝的「表現」彌補表相上的遺憾,「坦然」或「愧忞」無非就是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情懷。人生在世就是向歷史紀錄挑戰,有人一路追逐名氣,汲汲營營的追求功名利祿,企圖以留名青史為終生職志,藝術家的一生則是完全沉浸於他創作脈絡的歷史長河之中。違逆自性和良知的反其道而行之「非常」創作,面臨藝術史家展開地毯式的追索行動之際,「成名」於網際網路十五分鐘的傳播效益,足夠詆毀經營一世之英名,是以創作者的價值判斷絕對影響其作品的「品味」。
肖像是我的分身
黃素雲〈恩索爾藝術中的恩索爾〉討論比利時二十世紀初的重要藝術家恩索爾(James Sidney Ensor, 1860-1949)。恩索爾在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後完成的《基督進入布魯塞爾》作品裡頭,將自身化身為「基督」,以迂迴的手法暗示伸張正義的意圖與傳達個人的英雄特質。今年(2009)恩索爾的大型回顧展正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MoMA)展出,而不知是巧合或刻意,他最具代表性和富戲劇性的作品《基督進入布魯塞爾》卻在此重要場合缺席。恩索爾在另一件名為《危險廚師》的作品裡,卻捨棄了他「象徵式英雄」的化身,反而成為一尾在砧板上待宰的煙燻鯡魚,諷喻伴隨暗藏的控訴,已經是一種誇示威權征服「典範」的既定腳本,足夠讓觀者除了按圖索驥在畫面中找尋「像」或「像不像」之外,還需要運用到高度的聯想力,才有可能碰撞出藝術家暗藏在幕後的真正意圖。
藝術家創作雖非意圖滿足人們「窺視」的癖好,然而,藝術創作既然予人「生活日記」的印象,故而在日記裡呈現的意涵,往往被視為探究內心奧秘的重要依據。例如恩索爾以他「本尊」的立場,有時訴說一個被壓抑的辛酸故事,但多數時候恩索爾寧願化身成為「劇中人」,他可能只是扮演著一個微小到幾乎沒有必要存在著的重要角色-食物之一,但是重要的劇情演出若主角沒有了「他」,就無法突顯主角的存在意義,有了這個「調味品」,或許得以襯托出層級高於「微小」甚多的次要「配角」地位,於是戲劇性的一場演出,恩索爾的藝術所呈現的社會批判和隱喻,因而成功的侵入觀者的心靈。
眾裡尋「她」
長期從事「性/別」與「社群文化」研究的簡瑛瑛和彭佳慧分別從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 1907-1954)、潘玉良(1895-1977)、雪琳.娜霞(Shirin Neshat, 1957-)等三位藝術家提論〈性別.階級.族裔:跨國女性藝術的身分認同與自我再現〉,透過她們以「自畫像」或「自拍像」的方式創作的作品,探討不同族裔的女性藝術家如何以藝術「自我再現」?
「性別」的獨立自主與需否爭取所謂的性別「平等」的議題,自古以來即備受爭議。爭論迄今,上個世紀末熱門的「女性」議題,看待「性別認知」甚至持續有更多的關注面向,讓「自我認同」再次被提到舞台上,顯示了這仍然是當今民主聲浪裡一時無法避談的一環,而無論是否有所進展,這個議題短期間恐怕也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消弭。
墨西哥裔的女性藝術家芙烈達.卡蘿赫然成了這一期論文的重要焦點,選刊的兩篇文章,各以不同的議題討論藝術表現裡的性別特質與藝術家對待自我的態度。卡蘿原本只是一個懷有熱情追逐藝術夢想的女子,以「主角」的姿態成為她人生道路上扮演的「自己」和「角色」,同時呈現在平凡個體上的,只有以藝術的方法解決其糾纏不清的「本我」與「自我」,從如何「自我看待」逐步推進成為「看待我」,更加進步則變成「我」如何扮演「我」。
卡蘿崎嶇人生的戲劇性和劇情張力,本身就數度被搬上銀幕,而其中有許多藝術心理或是美術史觀層面值得探討的特點。姑且不論她的「性別認同」有否牽動它的創作傾向,卡蘿以自我形象完成的作品雖然不一定具備「自畫像」之名,其實是真正扮演著戲劇角色的「演出」,沉潛與外顯的「芙烈達.卡蘿」,表現在創作上卻十足熱情洋溢,她無疑的開拓了另一個世界的大舞台。
潘玉良在傳統的東方父權社會之生存機緣,隱約有她許多不能施展的「身分」問題。但是潘玉良飄洋渡海到了西方社會的發展,她自性裡強烈的「文化基因」卻無異於增強了她創作的能量,跨國、跨域的族裔情結成就了潘玉良在巴黎的創作,不但超越性別的刻板印象,超越了所謂的「時代環境」與「社會認同」議題的場域,轉化肖像畫作和自畫像背後的辛酸情感,「昇華」因而成為具有豐富文本的作品。
在不同的國度裡,雪琳.娜霞來自宗教威權強於「人權」的伊朗,相對於「神權」的至高無上,女性於爭取「性別」的社會地位和認同,幾乎被忽略、捨棄或視為微不足道的小事。娜霞將自拍作品賦予了新的訴求,如同潘玉良或者卡蘿用作品「發聲」的意圖,正是這三位「女性」用「藝術」超越性別、階級、族裔而展現「自我」的實證。
閱讀這幾篇文章所舉的個別案例,在客觀條件的排比下,三位女性藝術家來自不同的族群(或說是文化環境),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潛在影響,使得三位女性藝術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有「被壓抑的無奈與困頓」,但卻也不是絕對的具有代表性的象徵,轉換時空和立場觀察,因為在「邊緣性格」的驅策之下,她們超越自我的天賦和成就反而顯得精采。
驀然回首的自我再現
坊間談論性別認同議題的文章,以女性為討論的主軸,大多著眼於關懷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提昇女性之自主能力為要,文字論述和實質活動累積得也不少,相對的,無論是引述借題或另有企圖,從男性「角色扮演」成為女性作為議題,在繪畫表現當中的「性別意識」,相較於強調「女性」體態的誇耀,東方民族顯得中性溫和了許多。由東方男性扮演西方女性的這種變換角色的藝術創見,藝術轉化的力量和意涵必然超越視覺的「覺知」,當東方男性將自身模擬成為西方具指標意義的「女性藝術家」之際,我們看待這件作品的態度仍須回歸正軌,「認同」藝術的本體。
黃士誠提出論述日本藝術家森村泰昌(Yasumasa Morimura, 1951-)以裝扮墨西哥裔女性藝術家芙烈達.卡蘿作為諧擬對象的〈兩個芙烈達.卡蘿:森村泰昌之邊緣凝視〉,論文最後仍還原回自我「身分認同」的議題。黃士誠將兩位性別、國族和「原創性」與「對應力」極度相異的對象-芙烈達.卡蘿和森村泰昌並列,論述一個藝術家在面對紛擾的世間百態,反映於作品的內在嚮往。縱然眾所周知孿生兄弟的形貌相似,但是個性發展亦未必完全相近,甚至大相逕庭反倒是常有的事,但有意思的是,森村泰昌不僅從外在的視覺模擬卡蘿作品的「自拍像」,轉化為探討這位女性藝術家心靈底層的「性別(地位)認同」、「民族(文化)習性」等的歷史角色差異,森村所諧擬的角色還主動的詮釋了他「自我主張」的評價與隱喻。這個向藝術史作品借鏡並完全反轉的對照與解讀,更具體反映戲劇性效果和演出當下的時空情境也有關聯,除了東、西方先天的「自我」角色認知,尚且證明了「性別認同」的刻板印象乃東、西方皆然,甚至反轉了「自拍像」的意義吧!
古來不乏文人雅士用「心影」來訴說「內在的自我」,唐朝詩人李白在微醺的情境吐露心聲,「舉杯望明月,對影成三人…」對藝術家而言,影子和鏡像所反映的「形象」或是「意象」,傳達出其感應的虛擬幻景,甚且貼切地呈現藝術家內在的自我,「圖像」經常也比實際物質或「人物」更具有說服力。總之,精神的表象意義代表了最底層的自我,靈魂的感通彰顯其個別的特質,「自我認同」超越個性的精神層次和潛在性格,在爆發創作靈感時產生劇烈衝擊和轉折,映射表達「情境」的張力,呈現高度藝術境界的好作品即為明證。